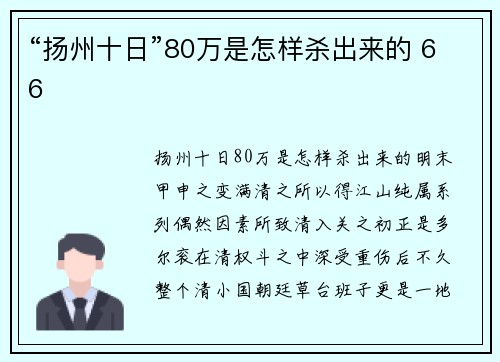“扬州十日”80万是怎样杀出来的 明末甲申之变,满清之所以得江山,纯属系列偶然因素所致。清入关之初,正是多尔衮在清权斗之中深受“重伤”后不久,整个清小国“朝廷”草台班子更是一地鸡毛。在摄政王多尔衮经洪承畴、范文程一番忽悠后,即使半推半就大军开拔到了山海关,仍是缺乏自信,因此,高调打出“驱除流民军,为崇祯帝复仇”的旗号,像模像样给崇祯帝戴孝三日,修缮明皇陵,操办独臂公主的婚事,从面上观之倒真是做了几出“孝子贤孙”的大戏,把个北京城惊愕得,还以为朱家一脉曾有王子去关外狩过猎,不打兔子,却干过小野猪呢。 清入关次年,1645 年开始举行乡试,第三年举行第一次会试和殿试,这对汉族士大夫来说无疑是明显的讨好。如此等等,在当时的北方,确实起到了稳定局面的作用。 彼时的北京人还是太单纯,野猪皮认朱明皇帝为“父”的下一步,不是为了认祖归宗,而是继承朱明王朝江山,进入紫禁城不再离去。显而易见的是,廉价的“认祖”仪式,就好像东北二人转一样,只能忽悠一时。何况闯王李自成风风火火进入北京城“42日旅游行”后,留下了崇祯帝的太子、次子、幼子,明朝的江山岂有被临时贴牌为后的贼子贼孙“继承”之道理! 就在这时,范文程、洪承畴之流发声了:且慢,要是崇祯帝的儿子人间蒸发了呢?多尔衮心领神会,于是,便将一直执念于三造明朝的吴三桂打发他去报家仇国恨,北京这里执行吴三桂与多尔衮达成的“盟约”第三条,北京归北朝。多尔衮这边则搜山检海把崇祯帝的儿子挖出来,就地当作李自成残余以物理方式秘密“做掉”。然后,继续演戏,让利于北京地区,不就把“名分”从无到有做了出来?如果“二人转”达不到效果,那就三人转,实在不行“全家转”,套裤子不行套裙子,涂胭脂不行就贴白纸,就凭一年365天,天天卖惨,焉有不成?! 就这样,人口庞大的汉人开始以静默观望的方式,给了清时间与机会,间接说明,崇祯十七年,北方士大夫对明朝已无好感,对崇祯帝的“勤政”更是厌倦。这对满蒙政权来说,正好休养生息,发展生产,稳定局面,创造出一个初生王朝的小兴盛。然而,不到一年,随着河北及周边不战而得之,抢劫得盆满钵满,野猪皮的后代们长出了“毛”,“队伍”野了,狂躁发作不仅愈发严重,更是成为一种常态。尤其是,满蒙政权在次年对南明发起的征战,几乎是走一路、屠城一路,一口气在江南地区“屠城”了十余座。有历史学者研究了“扬州十日”,十万鞑子兵十日屠杀80余万扬州人,并非一日完成,人均杀8人,日均杀0.8人,就难度上并非不简单。 问题的是扬州人怎么就任由鞑子把刀架在了脖子上,并不反抗?一队鞑子兵“搜山检海”进入一家民房,传递给居民的信息是,他们只是来“收租”、“收税”或者“众筹”的,拿钱赎命,给钱保家。待兵匪们榨干这家的钱财时,有鞑子兵背后使坏挥刀,像切西瓜一样,一颗颗脑袋顿时落地。有一队鞑子兵这样开了头,很快其它“收租队”积极跟进,不一日,屠杀居民就演变成了竞技游戏,兵匪的那仅有的一点人性一时之间荡然无存。 战争中,进攻方的官兵一旦入城,立马变成“匪”。“攻下一座城,劫掠三日”,这是一切非正义战争的潜规则。对处在游牧政权的满蒙政权,没有文化文明人性的影响,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赤裸裸的野蛮法则,官兵进城,抢到什么是什么,谁抢到是谁的。根本没有时间限制。这便是参战的红利,事实上“参战”只是幌子,参加“抢劫”才是目的,此所谓“从匪先从军”。对于游牧民族,发财靠抢劫是惟一的捷径。清军此次攻击扬州城因史可法的顽强抵抗,清军吃了些苦头,所以,攻进城后,“兵匪”的野蛮性来了一个彻底的爆发,一个个鞑子兵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禽兽,强暴文明,屠尽居民。 满蒙鞑子官兵的暴行,激发起了已和平安定繁荣了三百年的江南人,他们被迫拿起打狗棒反击,此时李自成张献忠幸存的流民军,在民族大义面前,纷纷抛弃成见,主动与南明政权联系,联手共同抵御清的野蛮血腥统治,维护民族大义,坚守文明底线,捍卫中华文化。 南明政权之弘光政权在被清血腥镇压后,不到一个月,南明隆武政权便冒了出来。他们保护家园,应者空前;他们文明传承,薪火不绝。先后连续出现了四个较有影响力的南明政权。可见,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,哪里有杀戮,哪里就有反杀戮。这便是清入关之后,反清势力一波接一波的主要原因。这叫强盗惹事,平民被迫应对。有意思的是李自成与张献忠的“残余势力”,居然成了反清复明的中流砥柱,可见,满蒙政权所挑起的匪情之残忍之残酷。 追根溯源,在于满清本身的铁血及无道。除此,就是那些卖身求荣的“贰臣”,他们同样坏透了。他们降低身份,一张笑脸凑上前去,下跪在鞑子的屁股下,要急满人所想,即使是满人所不想所不“急”,“贰臣”们也要“急”,而且争先恐后勇于“急”之。比如孙之獬的力主“剃发令”强行落地中土,这便是鞑子“扬州十日”后,劫掠屠城的有一个借口;比如洪承畴提议入关及剿杀最后的南明王朝,洪承畴第一次让内斗之后一地鸡毛的清小国走出困境,第二次让清小国统治中原;比如郝浴、李国英等挑起战端,祸乱巴蜀,人口锐减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 顺治十年(1653年),顺治受前明宦官吴良辅的煽动蛊惑,认为“内府事务殷繁,须各司分理”,因而建立起了专门的宦官机构——十三(B)衙门,把已废弃近十年的太监又捡了回来。他们共同所为应了那句:皇帝不急太监急,太监不及“贰臣”“急”。 于是,这才有了李莲英、张公公、小德子等去紫禁城谋职,专伺那里的男男女女出恭,从事着体面的营生,前提是“断子绝孙”。